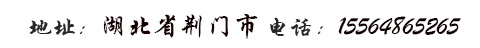田野风情野菜外一篇
|
有哪些医院治白癜风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a_zhiliao/160725/4910787.html 柔柔的清风总是催促我快去田野里,我也总是随着它,给自己找点事情,带着小姑娘,跑到田野去呼吸,顺手采摘一些大自然赐予的美味。 “妈妈,你快看,这是什么?”循着女儿的喊声,我慢慢的蹲下身子,仔细的观察着女儿眼中的那一簇簇有着红色茎和柔柔的叶片的野菜,他们一簇簇、一片片挨着静静的趴在田地里。这种野菜,在我的家乡是稀松平常的,我家乡到底把它叫做什么,这么多年过去,我在脑海里怎么回想,也想不起来了。 在这遥远的新疆,没想到也可以看到家乡的野菜,我也有点欢欣起来,摘起来一片叶儿,望着望着,仿佛就回到了小时候。那种馒头特有的香味好像也穿越几千公里、穿越时光慢慢的飘进了我的心肺,舌尖上好像也有了那种特有的香味。 好像是春夏时候吧,这种野菜总是在家乡的果园里、路边、渠沟旁,一大片、一大片的挤在一起,叶像马齿,所以它的学名叫马齿苋。它的茎总是柔软地铺在地上,叶子很小并且成对称地生长。 我奶奶总是做美食的好手,就是这种长在路边的野菜,她也总会做出很美味很可口的美食。记得她总是会将这种野菜和面和在一起,像是蒸馍馍一样团成圆圆的团子,放在蒸笼里蒸出来。 我总是会望着那袅袅升起的蒸汽早早的期盼着美味的菜团子,时间在满心的期待里过的总是特别的慢。奶奶总是会笑我,看你馋的。 等奶奶将锅盖揭开的时候,一大锅的蒸汽撒了欢的就冒了出来,我却把眼睛总是盯着锅里的野菜团子。那带着点热、带着点粘,野菜和着面的菜团子,那么诱人。 我拿一个起来,轻轻的咬一口,粘粘的带点野菜特有的清香,特别有嚼劲。不过,最喜欢的还是就着奶奶砸的蒜汁吃。那种美味,总是在记忆的时光里,难以再体味。 几千公里的路程啊,那般遥远…… 阳春三月,广袤的关中平原大地上,大片大片的冬麦都绽放了春的舞姿,不知疲惫的迎风舒展着腰身,随处都是提着笼(家乡一种树枝编的筐子)的小孩,好像比赛似的。 大家总是争相去麦地里去挖野菜,麦地里的野菜总是很多的。 但是,我记忆中的大抵只有两种。 一种在我们那里叫羊蹄甲(灰灰草),诚如它的名字,外表一点也不出众。灰灰的绿,总是像蒙着一层灰尘似的。 还有一种好像是叫地菜吧,它的叶子有些尖尖的,时隔多年,我的记忆都有些模糊了。麦地里,拿着铲子,满麦地里跑着挑,那会好像麦子是不怕踩的,我们总是在麦地里跑来跑去,提着笼跟这个比一下,跟那个比一下,总是比着谁挖的多。 要是谁挖到一个大的野菜,总是会惊呼一声。哇,这么大!我们就会激动跑过去围在旁边看,也不禁跟着惊呼起来。哇,这么大啊,总有成人的手那么大了吧。 哇,要抢了!大家嘻嘻哈哈的声音就那样飘散在云淡风轻的童年里…… 天快黑了,望望笼里的野菜,那么多了,都是压瓷了一遍又一遍,实在都压不下去了。眼看着筐子都满溢出来了,大家才吃力的挎着筐子从麦地里出来。回去的路上,还要追着跑着抓别人一大把。 等回到了家里,总是会自豪的将劳动果实展示似的倒在空地上。一大堆的野菜就是那份独特的美味,等着妈妈一个一个的摘掉发黄的叶子,清理干净泥土,再将这两种野菜分开来,分着分着就出来了草啊,麦苗啊,放在水里淘洗干净了,再放到筛子里晾干。等到了隔天,总是会吃到那独特的香味。 地菜经常只是下锅的时候当成下锅菜,稍微带点苦,但是拌着面食吃起来确实很清香的。灰灰菜总是会被做成菜疙瘩,和着面粉佌在一起,也是放在锅里蒸,蒸出来就成了香喷喷的菜疙瘩了。浇上蒜汁,拌匀,可以当菜吃。酸辣绵软的菜香就那样满溢着嘴巴、齿尖。 至今我还是没有学到这美味野菜的做法,总是会觉得遗憾。隔着千里的电话,我总是想问问妈妈这野菜疙瘩是如何做的,如何把握菜和水、面的多少。但多少次话到嘴边又开不了口,一股难言的酸楚涌上心头,又强忍住,又岔开去说别的开心的事。 太遥远了,总是不忍让妈妈对我多那一份牵挂与思念。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,我总是会望着窗外的天空出神,总是会想念我家乡那广袤无垠的原野。在这城市中待得时间越久,我越是怀念那泥土的芬芳和原野上的春风。 闲暇的时光里,我总是会带着小姑娘,去往野外,带着她,寻访妈妈的童年。看着她,好似又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,看着她在田野里快乐的奔跑,看着她吹着蒲公英四散飘散开去,就像是乘着蒲公英的种子又回到了我的关中平原。 乡愁 时间的车轮总是不会去管你愿不愿意,它始终朝着一个方向,永不知疲倦的转啊转,转啊转。 已经是年了,距那年上大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3年。13年的时间,在人生的长河里,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短了。我在新疆已经待了13年,这13年里,我的耳边总是不自觉地回荡起那首《乡愁》: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…… 自从踏上这遥远的土地的那刻起,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。虽然家乡给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,但我依然那么思念它。它始终好像跟随着我,让我在某个睡不着的夜晚翻来覆去的想念它,努力去想它在我印象中的样子。 我的家乡在关中平原,帝王将相给它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和王者的霸气,简单平实的生活被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过得踏实而富有生气。古时留下的许多习俗,让家乡在许多日子里热闹、欢乐。对家乡那种思念,就像是一根头发丝,时不时的在我的心口拨拉两下,不疼但是有牵绊。 记忆中的那条路,路两旁全是苹果树。苹果花开的时候,那条路分外的美丽。骑着自行车,徜徉在花海中,上学,回家,后来就是顺着那条路远离了家乡。 少年时代,对家好像没那么多的依赖。直到好多年以后,离开家乡到了千里之外求学,才发觉自己是那么依恋那个从小长大的家,那么依恋家乡的那条小路,依恋那些曾经在那里度过的童年时光和少年时光。 每年三月份,是家乡一年一度的庙会。各个村镇的人都会从四面八方赶去,热闹非凡。庙会上有耍杂耍的,有摆摊卖东西的,有老太太诵经念佛的,更是孩子们争相要去玩、去吃的地方。南来北往的声音夹杂着小孩的叫声和大人此起彼伏的交谈,构成了庙会的主旋律。 记忆中,婆(老家对奶奶的称谓)总是会给我在庙里求一根被佛祖开过光的红绳,绑在我的胳膊上,保佑我平安。那根红绳上承载的也是婆那份深沉的爱意。多年以后,我与婆相隔千里,我总是在梦中想到那个她给我绑上红绳的场景,泪流满面。 童年的夏天,知了使劲在叫着,一帮子中午不睡觉的小孩,总是拿着竹竿和塑料袋做的网子去抓知了,一套一个准。直到现在,我还是很怕这种动物。 小时候,只要下过雨,地上有薄薄的小洞口,这种洞口里一般都会有蝉的幼虫。几个小孩就用一根小棍子伸进洞里,然后用手捂上。蝉的幼虫以为天黑了,就顺着小棍子往上爬,这样抓蝉可以抓很多。抓回去就用碗把它扣起来,等第二天早上起来,蝉已经长出了薄薄的翅膀,通体发白。但还不是黑亮的颜色,再过几个小时,它就可以飞了。飞到树上去就开始知了知了的叫着,我是最怕这种动物的,从来不抓,别的小孩抓的时候我都是远远的看着。 这儿,夏天听不到知了的叫声。而家乡的夏天,就是知了那没完没了的叫声。 记忆中,还有儿时的那些小伙伴。那会儿,我们那么喜欢玩升级,一种纸牌游戏,四个人玩。我们总是坐在巧彬家门口,四个人东西南北坐定,只是谁也不愿意坐在南北两个方位。因为,我们总是说着,坐南北,输到黑。 彼时的三个小伙伴,一个留守家乡,一个去了遥远的青海,而我,则到了祖国的最西北。 再见,不知是何年。 还记得我们三个中唯一的男生,举着剪刀手给我们两个女生唱着:我是女生,漂亮的女生,我是女生,爱哭的女生时候的样子。我们两个笑的跟傻子一样。 那些曾经的欢歌笑语,都揉碎在了时光里。 还记得从学校骑着自行车回家的那条路上,突然迎面冲过来了一只大绵羊。当时脑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,我想着羊总是会给我让路的吧。结果,羊没那么想,直接冲着我就过来了。砰的一声,我就和羊撞上了,从自行车上摔下来,脚扭伤了,疼的我坐在地上哭。 至今还是想不通,当时我怎么会认为一只羊会给我让路。 还记得那年离开家时,妈妈送我到车上,隔着窗,车启动的刹那,她落下的泪。大概妈妈心中也是疼的吧,只不过她不愿意束缚自己的女儿,让女儿按着自己的想法去生活,她才不去牵绊我把。 看到妈妈眼泪的那刻,我真的不愿意走了,转过头的时候,我也泪流满面。但这么多年,我也总是学会了把心里的疼隐去,自己啃噬。 小时候,总是不理解那句父母在,不远游的游子诗篇。等长大理解了,却晚了,回不去了。 王蕾,笔名秦岭,陕西人,现在兵团四师工作,爱好文学,但疏于动笔,年过而立,忽觉在文学的道路上需笔耕不辍才能有所建树,即动笔写思乡之情,写塞外伊犁。 已在伊犁晚报、伊犁垦区报和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yangtijiaa.com/ytjhy/8162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前沿科技中科院等科学家合作在豆科系统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