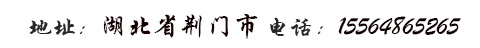微虚构白周涛游猫,或殒身不恤者的故事
|
PhotobyClementFalizeonUnsplas 编号 微虚构 本期作者白周涛 白周涛,九〇后,西安人,现居北京。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。有作品见于文学期刊。 游猫,或殒身不恤者的故事 白周涛 没有。原来没有猫。是第二批或者第三批移民潮带来的猫。这时我在想那些墨西哥有梦游症的猫咪。 ——罗贝托波拉尼奥《护身符》 朱雨一把打掉我的手机,说她得下楼去看猫,问我要门禁卡刷电梯。我没敢迟疑,在兜里踅摸出那张橙黄色的卡递给了她,而后翻身从沙发上起来,趿拉着拖鞋,跟紧她穿过门廊,走到电梯口。她摁亮感应按钮,回头对我撇撇嘴,说,不要跟着我。我就回去继续看美剧了。朱雨是因我回家晚在闹情绪。这我知道。我还知道她并没有为此而真的动了气。 我们刚吃完晚饭,一顿所谓膳食平衡的粗粮套餐。三根水煮当季甜玉米,一包g猪肉馅速冻水饺,两盒标有产地为科尔沁的手撕风干牛肉,以及朱雨手工腌制的泡菜一碟。当这几样东西从她的嘴里蹦出来时,它们听上去美味、健康且最为重要的是分量不少。当然难以否认的是,她的描述生动有力,温情感十足,足以抚慰人心,但当它们被置于盘子,搁上桌后,我开始后悔。等吃完那盘看上去最为管饱的饺子后,我的后悔俨然于脸上,并愈发难以遏止。 朱雨清楚我的食量,也熟知我的饮食偏好,重油重盐重辣重碳水重卡路里,每次吃饭碗里都像是打翻了酱缸,齁浓齁浓的。为此,她常常拉我一道茹素,吃沙拉,喝蔬菜汁,眯缝着眼睛灌盐水……深夜躺在床上,嘴里滋味寡淡,胃里空荡荡的,间或还会咕呱乱叫。我时而会吊着嗓子,拖长了尾音,假意哭丧。她捂住我的嘴,说,不要声张,陈哥回来听到不太好。我说,两只兔子精躺床上挺尸,他有什么大惊小怪的,何况宋总那边天天晚上喝大酒,他得候着,指定回不来。她一巴掌拍到我的肚脐眼上说,那也不行!我说,姑奶奶,我想吃肉。现在这样子,没法亲就不说了,一打嗝,两张嘴都能冒绿泡,像是隔壁躺了只反刍的德昌水牛。难得的比喻,她说。我叫嚷道,这不是重点。朱雨一只胳膊支棱起来,架高了脑袋说,这当然不是重点,重点是你知道27俱乐部么?我承认,她要命般的严肃拽住了我,但我从没听说过这玩意儿,心里觉得大概是什么夜店,但她的神情显然不太可能指向于此。我只能摇头。摇完头后又担心冷场,怕她不高兴,我问,这是个什么沙龙?你讲讲呗。她躺平,叹了一口气,说,也没什么,一帮不尊重生命的人而已。我听完,更加不解了,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,巴巴地望着她。偏偏,她又不说话了,只是慢悠悠地背转过身子,似乎是没有听到一样。过了很久,她拉过我的手,摊开来,摆弄了几下,十指相交,郑重地握紧,开始说话。 她告诉我,她爸以前是鸥城国营鞋厂供销科科长,专门负责两广片区,为此,常喝大酒,习惯性熬夜,饮食也没规律,胡吃海塞,加之缺乏锻炼,五十岁不到,人就中风了。我捏紧她的手,问那是怎么一回事啊?她说,怎么说呢?就是晕过去了,不省人事了,一时半会动弹不得,得有人在身边,不然就要了命了。我听得饶有精神,干脆弓起上半身,腾出只手,拍拍她的脑袋说,我姥爷也得这病,不过我那时候年纪太小,压根记不住犯病是啥情形。她抬起腰身,往我怀里拱了拱,说,很不巧,我碰上过,那场面挺让人别扭,而且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。 具体是有次半夜,她饿得受不了到冰箱翻东西吃……我手指尖戳了戳她的肩胛骨,按住话头,盯着她说,这可不像你现在的风格。她哂然,打掉我的手说,她那阵子在学芭蕾,要代表学校参加省里的育禾大赛,老师叮嘱过她爸妈需要节食一段时间。可她那时候正长身体,加上日常训练量巨大,胃一空就难受,尤其是吸腿拧腰和后下腰两个动作。讲到这,她还下地,在橡木地板上比画了两下。你看啊,就这两个动作,吸腿拧腰和后下腰,前者需要坐在地上双腿伸直,左腿弯曲,左脚紧贴右腿小腿肚,后背挺直,向左后方拧腰。而后者必须右手扶把杆,左臂向前打开,上举过头,向后下腰,尽量将双肩放平,后背部收紧。两个热身动作,不到六个步骤,她呼哧嘿哈的,头上的吸顶灯似乎都在跟着震动。等比画完了,朱雨喘着粗气说,真年纪大了,不行了,以前一整套三十多个动作做下来都不带喘的。气韵平息后,她接着说,两个动作很基础,不怎么费工夫,也没什么技术要领,但是空腹愣上,任何训练者都撑不了半刻钟。所以,那段时间她自己制定了加餐计划,自己给自己加,每天定了闹钟,趁爸妈睡上半个小时后,偷摸着去冰箱挑拣着吃。那天也是,她说,她刚旋开草莓酱的瓶盖,正窸窣地拆面包包装纸的时候,听见隔壁房间抖抖索索地一阵响动,像是有人用指甲来回剐蹭脚踢线的木板。起初,她没太在意,以为是老鼠,可家里住在高层,怎么可能有老鼠,想不通。嘴里一边悄声念叨,一边舔着面包片上的草莓酱,压根没当回事。可那声音就是挥之不去,轻飘飘,但富有规律、挠人心神。她按捺不住,径直走过去推门。果然,门推不到25度锐角,就打不开了,探出头一看,心里一颗石头落下去,一颗更大的浮了上来。彼时,她爸趴在地板上全身抽搐,双腿快拧成麻花了,嘴角下噙着一串白沫,正在用弥留之际的最后一点儿知觉抠地板……后来又犯病,反反复复,并发症添了一大堆,肺炎,肾衰竭,中耳炎,全身无力,陆陆续续的,感觉能得的不能得的全给得了,倒也都不是什么绝症,就是折磨人。老头到后来,一犯病就抓着床褥猛撞后脑勺,也不顾及形象了,无论身边谁在看,嘴里夹缠不清,囔囔地,怎么不去让他死了算了…… 她讲得很投入,我不敢做声,也不好打断她,只能一味去听,任由她的手越攥越紧,屈弓着麻痹的胳膊也不敢随意动弹,仅仅是在她讲到动情深处,抽泣之时,揽过来,紧紧地抱着她。不过,我听朱雨提起过,伯父并没有因为中风而怎样,反倒是和伯母坐车回瓯城时,夫妻双双折在了一场没来由的动车事故中。这件事快过去八九年了,朱雨已尽其所能地让生活走上正轨,恢复如往常一般的秩序。我知道这不容易。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她家做爱后,看着空荡荡的三室两厅,我问及她的家人。她指着客厅墙上的相框说,喏,你看,都在那呢,两口子,整整齐齐的。 与我不同,朱雨是地道的南方人,皮肤白皙,声音温软,就是脾气不大好。最近她的女上司早产了个男婴,她们工作室的人都去看了。去之前,她还问我带什么礼物感觉庄重而不俗气。老实说,我对送礼一窍不通,给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建议,上网搜索后,罗列了一张单子给她。最后她选了礼盒装的阿胶以及一本平订胶装大十六开本的油画册。 直到下午五点钟那会儿,她们一医院的单间里拉扯家常,朱雨给我发了一张婴儿照,说,看样子没法一起回去了,大家都在逗弄孩子,我走不开,你不要傻等在科苑地铁站了。我那会儿正结束一个通告,在报社旁边的咖啡馆里码了五千多字的一个人物访谈,完事后,提交给了北京的后台编辑,编辑收到后,没有回复,我想她可能在开会什么的,就没有贸然去问,只是安静地喝完了那杯用来提神的美式。我定了定神,端起手机,回复到,贵司可真行,孕妇病人最需静养,你们倒好,看望反倒成了添堵。她回复了一个捂脸的表情包,没再说话。我低头确认了一下时间,又看了看沙河西路上拥堵的车流,想着没有必要随大流去挤那个人潮,遂决定回社里呆一会儿。 外面的天空蓝得透彻,空气洁净而鲜活,路两旁蓊郁葱茏,草木葳蕤。蓝花丹泛着浅浅的蓝色,蓝得发青,蓝得发白,使人冷淡而忧郁。除此,还有朱蕉,巴西鸢尾,羊蹄甲,金合欢,鱼尾葵,它们一丛丛,一簇簇,汪洋而恣肆地生长着。道边栽植着茂密的高山榕,树冠巨大,气根四处纵生,蓬勃旺盛,顶的人行道地砖松动,路面坑坑洼洼的,很不好走。我一边提防着垂下来的榕树气根,一边跳着避开脚下的积水坑,心里打趣自己回到了丛林时代,需要人猿泰山的矫健才能安然无恙。就在我想得入神时,一身臂膀黑黝黝的莽汉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以为对方是要问路,摘下耳机问他,有事吗?话说出口,觉得有点冒失,不太尊重,毕竟对方四五十岁的样貌,是父辈人。心里想着,嘴上含混着,拖长尾音,加了个您。他腼腆起来,脸上横肉挤出一道笑容,褶子之间埋着无数粗大的毛孔,他说,小兄弟,你能帮个忙么?我听完这句话,转身就要走。他叫住我,开始用蹩脚的徽普说话。他告诉我,他是安徽阜阳临泉人,来深圳有一段时间了,交友不慎,自己身上的钱都被骗光了,这两个月,他一直在对面的工地上做些杂活,下午午睡起来后,忽然发现身上没有一分钱了,而这个工地的人都是湖南的,没人肯帮他。他说,我实在走投无路了,要不然也不至于这样,当街乞讨。他说着,从口袋里拿出身份证,双手捧着,让我相信。我眯缝着眼睛端详他,中年人,个头儿不高,一米七出头的样子,四五十岁,微胖,有肚子,平头,皮肤黝黑,带着一股淳朴的田园风。委实说,他长得过分的不起眼,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,愁容满面,尤其这会,眉头紧锁,目光柔和而呆滞,不像是犯事或者能惹事的人。我收起他的身份证,看了两眼,觅到一个叫陈亚伟的名字,没觉得有什么特别,便塞回给他,只叫他跟着就成。 到了便利店,我按他说的,买了些吃得喝的。结完账后,我告诉店员,有热水啥的,可以给备一点儿用。说完后,我径直走过去推门,并没打算获取一点儿慰藉人心的感恩,因我从未高看过恻隐之心带来的好与坏。未及预料地,他在后面拽住了我。我转身去看,依旧是此前那副唯诺的表情。他嗫嚅着说,能不能买包烟。我有点不耐烦了,哼哧着粗气,摊开手问,why?柜台里的店员瞥过来,似乎把他当成了我的长辈,看我的眼神怪怪的。我想快点结束这一切,只好冲着那个大妈年纪的店员指指烟架,大妈心领神会,走过去拿了一盒黄金叶。他摆摆手,说,要华子。我蹿了起来,浑然不顾自己的形象,跳着脚说,你差不多得了,还蹬鼻子上脸了,咱俩压根不熟,我敬你是条汉子,给你买点儿东西,有点儿意思得了,咱俩起码互相尊重,可你现在这是玩哪儿出?把我架在炭火上烤?有意思吗?我一口气说完了所有话,像是打光了一梭子弹,畅快淋漓。 他没再抬头说话,我看了看,推开门扬长而去。 回到社里,我感觉心情有点儿不快,想找人说说话,四处转了转,看到平时最要好的财务小哥下班走了,商务部门能说会侃的也走光了,只剩几个老家伙还在绞尽脑汁地攒稿子。见到我,他们打了几句哈哈,问我今天访的那个慈善大使怎么样?我说,有点儿意思,可又没有那么有意思,说鸡肋好像有点过分,毕竟捐了几个亿了已经,总之是个很无趣的中年男人,实现了世俗定义中男人成功的一切,现在正开足马力朝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进发。我寻了几个他个人自传里称之为里程碑式的节点,用华尔街日报体那套,将他五十多岁人生大体串联了一下。成稿让他很满意,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yangtijiaa.com/ytjxt/1131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总状花羊蹄甲植物非试管高效快繁
- 下一篇文章: 微虚构白周涛游猫,或殒身不恤者的故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