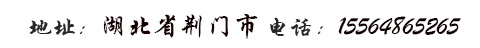招魂哨
|
北京皮肤病最好医院 https://m-mip.39.net/pf/mipso_6084108.html 最近又在计划着进藏,便想起我十五年前写的这个西藏故事,承蒙朋友们厚爱,它曾经拿了两次网络大赛的金奖,年底,深圳电影制片厂找上门来,买了它的影视改编权,签了5年,到了,依然没拍成,版权又回到我自己手上。最近翻出它来,跟故事中的关键人物——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贺中老师对齐了一下,贺老师帮我补充了一些细节,我又改了几千字,让它更接近真相,再次呈现在朋友们面前。别管是真是假,就当小说看吧,若有相中的朋友,我可以再卖。 01 年9月3日晚,在拉萨,八廊学客栈隔壁的“念”吧,我陪一个艳遇未遂的女孩,等一个来跟她赴约的男人。 万万没想到,我差点因此命丧拉萨。 那一夜的念吧,上半场是这样的 那是我第一次进藏,既是旅游,也顺便拜访一位前辈——贺中老师。贺老师是跟马原、扎西达娃同时进藏的作家、诗人,也是最后留下来的一位。可当我到了拉萨,才得知他已到墨脱采风去,要几天后才回来。我决定先在拉萨周边逛逛,毕竟,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,每一个角落对我来说都充满着新奇。 说来好笑,我是被那女孩捡上的。背包客进藏,拉萨是目的地也是集散地,客栈都有供散客临时组合的留言板。9月1日早上,我本想去山南,正在八廊学客栈看留言板,身后响起一个清脆的女声:“林芝三缺一,即走,还有谁哈。” 转过身,便看到一个穿迷彩服的女孩,双手叉腰站在客栈院子里大喊。娇俏又强悍的画风,高原的阳光打在脸上,把精致的五官涂上一层迷彩,给青春底色加了不少饱和度。 鬼使神差,我想都没想便喊,我去。 女孩也爽快,手立即伸过来:“我叫林汐,双木林,三点水夕阳的夕,大哥怎么称呼?” 我伸出手,礼节性地跟她握了一下,“余少镭,多余的余,多少的少,镭射的镭”。 去林芝路上经过米拉山品,这是林汐为我拍的四个人临时组合,包了辆去林芝、鲁朗看林海,三天两夜。除了林汐和我,另两位是一对情侣,林汐跟他们也是临时组合。路上,我和林汐的话也就多了起来,聊天中,知道她孤身从成都来,在西藏呆了大半个月,林芝是最后一程。 美丽、爽朗,还善解人意,青春少女的气息扑面而来,我有点五迷三道了。 在林芝的那个晚上,为省钱,四个人开了一间三人房。林汐的床跟我相邻,也许是高反还没完全过去,她倒头就睡,对人全无戒心。在她均匀的呼吸中,我彻夜难眠,不时转过头偷看她那精致的五官,想象被子覆盖下的珠穆朗玛……那种甜蜜的煎熬,终身难忘。 鲁朗林海(没特别注明就全都是我拍的)白天,鲁朗的林海如仙境。美景、美人,再加上睡眠不足,我时刻沉浸在迷醉之中。不过,凭狼一般的直觉,我判断,这趟应该没啥戏,因为,颜值实在相差太大,我一路耍嘴皮子,抖小聪明,最多是她不讨厌我而已。旅途上清风朝露般的艳遇,基本是由双方颜值差决定的。明白了这一点,顿时轻松起来,就当个三天的旅伴,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艳遇。 3号那天,从林芝回拉萨路上,林汐才跟我说,她已订了明天回成都的机票,今晚是她在西藏的最后一夜。我惯性反应,说那给个机会我请你吃饭吧,就玛吉阿米。她说行。 玛吉阿米位于大昭寺后面,传说是西藏历史上特立独行的六世达赖、诗人仓央嘉措私会情人的地方。因为这个浪漫的传说,玛吉阿米成了来拉萨的文青打卡地,暧昧浓度堪比酥油茶。这最后的一丝机会,对我来说无论如何不能浪费。好像鲁迅真说过,希望本是无所谓有,也无所谓无的,这正如西藏的路,西藏本没有路,想艳遇的人多了,也就有了路。 八廓街上的玛吉阿米。外观不咋的,可是文青打卡圣地 可是,当我试探性地提出饭后去泡吧的时候,林汐给了我致命一击:“其实,那啥,余哥,今天晚上,知道我明天要回去,一个男生特意从亚东赶回来,想再见我一面。” 也许是没看到我的目瞪口呆,也许是对我的沮丧视而不见,林汐一边摆弄着咖啡匙,一边将他们的故事告诉了我。 “我跟他,也是临时组合去纳木错时认识的。那儿海拔近五千,我高反厉害,他照顾我很细心,给我讲笑话分散注意力,又花几倍价钱跟别人买了氧气袋给我,甚至在帐篷里把羽绒服让给我穿,自己挨冻。我过意不去,便让他抱着我……真的只是抱,就这样在湖边的帐篷里过了一夜,他还是很尊重我的。回到拉萨,因为他事先跟别人约好去亚东,我没那么多时间,就和他就分开了。咱去林芝的时候,我跟他一直有短信联系,他都说他在亚东,想过尼泊尔去。” 这事搁以前肯定不信,现在我信了。在西藏,每天都有这样的戏在上演,区别只在于,你入戏后,多久能出戏。 “可是,他听说我明天要回去,居然放弃尼泊尔的行程,一定要赶回来再见我一面。我都跟他说不用了,回成都后会跟他联系的,可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事,与我无关。反正,今晚11点前一定赶回拉萨。你说这是不是很变态哈。” 林汐说“变态”两字的时候,脸上甜蜜满溢。 她之蜜糖,我之砒霜。 决定换一种策略。 “太感人了,”我说,“那必须等他,这样的男人,世上少有了”。 “如果是你,你会这样做吗?”她突然盯着我问,眼睛里仿佛倒映着雪山圣湖,那语调,又像极了周迅对贾宏声说的:“如果有一天我走了,你会像马达一样找我吗?”那一刻我突然想到,这会不会是她编出来的故事,目的是拭探我……于是我决定剑走偏锋,便说,不会的,我才不会这么傻,没错,你很漂亮,正常男人第一眼都会喜欢你,我当然也不能例外。但是,漂亮女孩到处有,而藏地每一片风景都独一无二,我难得来一次,怎么可能为了人间的美色,而舍弃天堂般的美景。 “也是。话说,我该不该说谢谢你的坦率呢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她嘴角微微一翘,说不清是尴尬还是讽刺。想了想,又说:“换我也是,可他怎么就那么傻呢?”她像是在自言自语,过了一会,脸上又露出甜蜜笑容:“不过他可真帅,特像吕良伟,吕良伟你知道吧?” 我笑了,我可是看港片长大的,原来他那么帅,难怪。 说完这话,我起身走进洗手间。倒不是要撒泡尿照照自己,洗手间有的是镜子。在镜子里,我看自己,身高长相,怎么看都像是猥琐版曾志伟。曾志伟在电影里也有甜蜜蜜的爱情故事,但那是戏,西藏再怎么浪漫,终归是现实世界。 那一夜的玛吉阿米,我希望破灭之地 从洗手间出来时,林汐皱着眉说:“现在我纠结的是,不知去哪儿等他好。在我房间吧,我觉得还是不大好。再说,我们那客栈很早就关门,万一他半夜还赶不回来……可是,在外面等,我又不知去哪儿好。” 我说那跟我走呗,刚就说过嘛,我还是陪你去酒吧等他吧,就我们住的八廊学旁边那个念吧,那里驻唱的乐队,野孩子,很棒,咱一边听歌一边等,你放心,他一出现我就离开,我只是担心,你一个单身美女,在外面太晚了不安全。 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,有一种失败,叫做扮崇高。 02 事发前,我跟野孩子乐队的合影,左是张佺子夜时分的“念”吧,野孩子的演唱已结束,酥油茶香在烛光中氤氲。我陪林汐坐了三个多小时,喝光了两壶酥油茶、四罐青稞啤酒,把其他客人都熬走了,“吕良伟”还没有出现。要不是林汐不停地跟他发短信,我真会以为这是她编出来的故事。 “他说他过康马了。”“他在江孜换了车,原来包的那车坏了。”“啊,不会吧,在卡如拉山口居然遇上雪崩!车已堵了一个多小时,天,这得什么时候才到啊!” 我一边安慰着她,一边在心里估算着路程。亚东属日喀则,位于中印尼边境,离拉萨五百公里左右,路是不大好走,可他下午1点就起程,11个小时了还走不到? 失望,甚至开始觉得有点无聊。但我已把这事当成一场戏,自己选的角色,含泪也要演到谢幕。 不知不觉中,我吹起了口哨。 很多时候,我的口哨完全是在自己无意识中吹出来的,这一次也是,我是先发现我在吹,继而才听出来,是那首不知名的西藏民歌: |||-| 这首曲子,忘了是什么时候听到的,旋律反反复复只是这一句,魔性,入脑。 在这深宵的拉萨,在我喜欢的女孩面前,我被自己的行为和哨声感动了。 哨声中,酒吧里出奇的静。可惜,林汐明显没被我的口哨吸引到,“要不我们回去哈,服务员都困了。”确实,那个叫什么丹姆的藏族女服务员,已趴在桌上好像睡着了。 “他确定来不了吗?”我问。 “都说了几次快到了还是没到,要我等到啥时候啊。”林汐真的不耐烦了。 “那算我要等他好不好,我真想看看,当今世上难觅的情种长啥样,要回你先回去。”我的口气已像在跟自己赌气。 林汐嘴一撅,正想说什么,酒吧门帘忽然一动,一个人走了进来,径直走到我们面前——不是“吕良伟”,而是一个藏族老人,七十左右,穿着最常见的藏袍,古铜色的脸皱成一把,腰有点佝偻,胡子拉碴,身上却没有那种复杂体味。 “刚才那谁吹口哨是在?”老人瞪着我们,用生硬的汉语问,口气有点凶。 “我,怎么了?”我警惕起来,林汐脸上也现出恐惧的神情。 老人打量了我一眼,叹了口气,欲言又止:“这位客人你不知道,吹口哨那啥是……唉。” 这时服务员丹姆也醒了,走过来跟他打招呼,看起来很熟的样子。两人用藏语说着什么,听那语气和手势,老人像是在责怪她。果然,丹姆转过身来对我说:“不好意思先生,我刚才睡过去了,忘了跟您说,我们这儿,夜里是不能吹口哨的。钦顿大爷在街上经过,听到您在吹口哨,才进来提醒您。” “不能吹口哨?因为吵到人吗?”我问。 “这倒不是……”丹姆也欲言又止。 这就奇了怪了,我知道入乡要随俗,藏地有诸多避忌,我在旅途中都提醒自己不去触犯它们,可从来没听说过口哨也不能吹。 看我满脸疑惑,那个叫钦顿的老人对丹姆说了句什么,丹姆点点头,就去酒柜拿酒。老人坐下来,对我说:“远方的客人,我请你我们喝一杯,再告诉你,为、为啥不能吹口哨。”我看了一眼林汐,她倒不害怕了,一脸好奇。我说那谢谢了,不过,这酒我请。 酒满上,我们干了一杯。老人抹抹嘴,说客人是广东来的吧。我点点头,指着林汐说,她是四川来的,我们不知这里的风俗,多有冒犯,您多见谅。老人摇摇头说,你不知道,在我们这儿,夜里吹口哨哪,是、是会招来……是会招魂的。 招魂?不是吧。 林汐的眼睛突然间也瞪得很大。 老人说:“知道你不信,我呢,为你好也是。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,讲完了,你信不信都好,赶紧回去歇去。”我看了林汐一眼,点点头。老人又喝了一口酒,继续用那一口生硬的汉语,讲开了故事: 那还是文革时期,一个援藏干部被下放到我们牧区牧羊。我们那儿除了羊,就是风和雪,百里难见一人。那干部跟你一样,口哨吹得可好了,每天夜里都吹,不停地吹,哨声顺风几十里。我给他送饭时候就跟他说,您哪,千万别吹口哨,会招魂的。他说他是无神论者,不信这个,照例每晚都吹。 一天早上,他突然跑来我家找我,脸都是绿的,只说了一句话,出事了,拉起我就跑。我牵了马,驮着他到了牧场,几十只羊倒在圈里,全死了。他说夜里没风,没听到有啥动静,早上起来就这样了。我估摸到是啥事,便去看那些死羊。表面上,羊都睁着眼睛,身上一点血都没有,也没有伤痕,不像被什么野兽咬死的。我看了一会就发现,每只死去的羊,左后蹄都破了一个小洞,周围还有皮毛被烧焦的痕迹。我这一看就明白了,他的口哨招来了恶魂。你们不晓得,人的灵魂也分善恶,要是招来善魂就没啥事,招来恶魂就不得了,大祸临头。那干部的口哨招来的是恶魂,咬破羊蹄,把羊身体里的灵魂给吸走了。那些烧焦的地方,是灵魂极不情愿离开身体的时候灼伤的。 干部吓坏了,羊死了那么多,他本来就是摘帽右派,再套上一个破坏边疆革命生产的罪名,那可就不得了了。我本来想骂他不听我的话,吹口哨惹祸,骂了又有啥用,就跟他说别再吹口哨了,又教给他一个辟邪的办法,他对我的话再也不怀疑了。 果然,两天后,他高兴地对我说,有一天夜里恶魂又来了,他半梦半醒,看到一个白影飘了进来,趴到他床前,张开口就咬他的脚趾,他按我教的办法,真的把恶魂赶跑了,羊也安然无恙。 “啥办法?”我和林汐不约而同地问。 老人沉吟半晌,说:“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信。这样吧,我给你这个,你带身上,离开西藏前千万别丢掉。”说着,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皱巴巴的线条,捋开,递给我。像是一道符,深蓝底色,上面烫金印着一行藏文: 我突然明白了,呵呵一笑,掏出二十块钱放到桌上,说谢谢您了老人家,这算我的随喜功德,您别嫌少。老人愣了一下,看着我,突然怒了,脸涨得黑红,手往桌上一拍,说:“我活了一辈子,是这样的人吗?我要你的钱做啥子?你就要大祸临头了,信不信由你。哼,你们汉人怎么都这德性。”说完站起身,对丹姆说了一句藏语,丹姆一脸歉意,对他也说了一句什么,他又回头看了我一眼,气冲冲地出去了。 气氛有点尴尬。林汐嘟起嘴说,余哥我也觉得你有点侮辱他了,就算是你想的那样,也等他开口再给钱哈。我说你不知道,我到拉萨的第二天,就被俩喇嘛坑了。那时我高反刚有点缓和,第一次出来街上走,迎面走来俩喇嘛,还没到我面前就冲我合十行礼。我知道西藏有布施的风俗,就给了他们20块钱,他们收下钱,拿出一个挂着红绳的小红纸包,硬往我脖子上套。我小时候见过那种东西,是老人从神庙里求来给小孩保平安的符,一直就很排斥这种玩意儿,但觉得这是他们在表达谢意,拒绝太失礼,就硬着头皮让他们套上。没想到,套上后,他们又掏出一本子打开让我看,上面是密密麻麻的签名,每个签名后面,都写得或不等的数字。我心里有火,可俩喇嘛牛高马大,一前一后围住我,硬突围可能会付出更大代价,没辙,乖乖掏了一百块给他们,这才放我走。 林汐扑哧一声笑出来:“哈哈,你就是个哈儿,来西藏也不做功课。我告诉你,这些喇嘛基本都是假的,大都是从我们四川来的。然后,那符呢?” 我说早扔掉了,我可不想留着他,让自己一看到就想起拉萨街头被骗的经历。 “其实也没必要扔掉,虽然是假的,留着也没啥坏处,也算是你西藏之行的特殊纪念品嘛。” 我张嘴就撩:“跟你同行才是我西藏之行最珍贵的纪念品,其他的,能扔就扔。” 她突然伸出手,拍拍我肩膀说:“得得,余哥,我可不吃你这一套哈。” 那一瞬间,我肩膀如遭电触,差点就伸手把她的手握住,就那么一秒钟的犹豫,她的手已缩回去了。我只好转移话题说,所以我深度怀疑,刚才那老人就是编故事卖符的,类似的吸魂故事,我记得聊斋还是哪本志怪小说上就有过,我一直在写“现代聊斋”专栏,瞎编灵异故事,在我面前玩这个,那是遇到同行了。 林汐嘴一撅,说:“反正我就对你的无神论很有看法。你看你都来西藏了,这可是离神明最近的地方,可跟你在一起才几天,我就能感觉到你对神明一点都不尊敬,这样可不好。这事你得听我的,宁信其有不信其无,这符你得收起来,回到广州再随你处理,行吗?” 说这话的时候,她眼睛直视着我,里面满是温柔。认识了三天,一路相伴,我还没见过这样的眼神,可惜,有缘无分,徒唤奈何……我不敢再看她的眼,把符推过去给她,说:“那这符我转送给你吧,你这样经常出来的美女更需要神的保佑。” 她又一个坏笑,把符推回来,说:“得了吧,我可不会吹口哨,最多招蜂引蝶,不会招来什么恶魂善魂。余哥,你听我的,把符收起来,好吗?”说着,又用那能杀死人的温柔眼神看着我。 我彻底投降了,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,只好又故作痞气地说,得,美女面前不要底线,这也是我的底线,我听你的还不行吗。说着,把符随便一折,塞进牛仔裤兜里。 这时林汐看了一眼手机,兴奋地说:“哈,他终于回到拉萨了。” 03 那男人出现的时候,我看了看表,01:19。他裹着一股寒风掀帘进来时,我就知道是他了,目测身高一米八以上,古铜色皮肤,浓眉大眼,不但很吕良伟,戴上帽子简直就是一个风靡万千女文青的康巴汉子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,第一感觉,在阳刚的背后,藏着一丝隐隐的阴气。 也许是内心醋意在作祟,愿赌服输,我无话可说。 看到他,林汐站起来说:“你终于来了,都跟你说……”口气却没有我想象中的热烈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一旁的缘故。 “吕良伟”走到我们桌旁,朝林汐张开双手,也不说话,林汐看了我一眼,轻轻跟他拥抱了一下,很礼节性的,便分开了。 “妹子,这哥们是?”他指指我,终于开口说话了,东北口音。 “哦,我来介绍一下,”林汐指着我说,“余哥,广东来的,我们在林芝认识的。他知道你要来,怕我一个人在外面等你不安全,一直陪着我。余哥,这位是我跟您介绍过的,我在纳木错认识的慕容大哥,辽宁那旮的哈。” “你好慕容兄。”我做好握手的准备,他却不伸手,只是朝我点点头,算是打了招呼。我以为我会愤怒,但是我没有,都是萍水相逢,何必浪费宝贵的愤怒,他对我的警惕和冷淡,反而暴露出他的不自信。这么想着,我站起来对林汐说,那行,任务完成,现在没我啥事了,你们聊哈,我得回去睡觉了。 林汐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,“余哥您别这样,都是朋友哈,我们一起聊一会,等一下……八廊学没房了,慕容大哥可能还得住您那儿”。 这话谁信呢。我说抱歉你们聊吧,我明天还要去山南,得早起。说完,头也不回地走出酒吧。 一阵冷风从北京东路刮过,我打了个寒噤,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哆嗦着,敲响了八廊学旅馆的门。 那一年的八廊学,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,变成什么样了 回到我的,脸也不洗牙也懒得刷,就把自己扔到床上。 可是,越想睡越睡不着,脑子里乱成一锅粥,一些乱七八糟的文字、奇形怪状的影像,像秃鹫围绕着尸体在盘旋,有时是那老人给我的那道符,有时又是一些像来福线一样旋转着的线条,就像我刚到拉萨时高反一样。也尝试着数羊,但羊的形象在脑里一出现,随之而来的,便是羊蹄上被烧焦的洞……黑暗中,狭窄的房间仿佛在不停地变大、旋转,跟我咫尺之隔的另一张床,恍惚间也在旋转着漂向远方。不数羊了,那些羊却一只只挤进我脑里,还有一阵若隐若现的口哨声忽远忽近……我赶紧把头全部缩进被窝里。 不知过了多久,楼下又传来敲门声、开门声、上楼梯脚步声。不用猜,林汐和她的“吕良伟”回来了。我在被窝中看看夜光表,两点。脚步声经过我门前,走到走廊的尽头,拐了个弯就消失了。我知道,林汐的房间在那一头的。 这下就更睡不着了,脑子里全是他们开门、进门、上床的凌乱镜头,像一部剪辑错乱的AV,我想象着他怎么撕开林汐的衣服,把手伸进去,从珠穆朗玛到羊卓雍错……奶奶的,我甚至后悔今晚充好人了,搞得自己连个安生觉也睡不着。 睁着眼睛在黑暗中过了十来分钟,也许是刚才酒水喝多了,尿意如潮汹涌,忍不住,穿上外套,趿上拖鞋,打开门,沿着走廊向厕所走去。夜里两点多的八廊学一片死寂,暗淡的日光灯在走廊尽头气若游丝。头晕着,好像整个客栈都在摇晃,拖鞋声在空旷的走廊中显得格外碜人。 因为是青年旅舍,八廊学的厕所很简陋,女左男右,两门相对,连门扇也没有。走进里面,两个厕位才有薄薄的门板挡着。进了厕位,刚要拉拉链,突然,一声细细的啜泣,从女厕那边响起。我吃了一吓,差点就小便失禁。不用怀疑,肯定是刚到拉萨开始高反的女孩。高反的痛苦我是深有体会的,简直痛不欲生。 我走出男厕,朝女厕喊了一声:“没事吧朋友,需要帮叫服务员过来吗?” 没人吭声。 我瞥了一眼,女厕里连个人影都没有,只是有一个厕位的门好像虚掩着。突然想起钦顿老人的话,此情此景,再怎么无神论也会心里发毛。我只能安慰自己,对方应该也是被我吓着了。 走回厕位,拉下拉链,又一声啜泣从那边传了过来!我冲出男厕,啥都不顾了,站在女厕前,大声壮胆三连:“有人吗需要帮忙吗能吱声吗?” 虚掩着的厕位里有了动静,一丛头发从门扇后升了起来,接着是头、脸——竟然是林汐,她还穿着刚才在酒吧里那身衣服。 “余哥。”她走了出来,看着我,眼里泛着泪光。我心里一扯,你怎么了,高反还是?她摇摇头:“余哥,刚才我就想去找你,又怕你睡着了,不好意思打扰,只好躲到这里来,没想到……” “我的门一直向你敞开着啊,出啥事了?”我隐隐猜到,可能跟“吕良伟”有关。 “余哥,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?”她低着头,欲言又止。 “咱还用得着客这个气吗?”我急了。 “我想……我想让他到你那屋睡,八廊学房间都满了,我知道你住的是双人间,行吗?真不好意思。” 是,我入住时单人间都满了,只好要了一个80块钱的标间。 “当然没问题,可是……可是我以为,你们……”我心里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感觉,说不清是高兴,还是幸灾乐祸,反正,像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失而复得。 林汐尬笑了一下,“余哥,我不是那种女孩,虽然,虽然我对他有好感,也不排除以后会跟他继续处朋友,可在这样的情况下……我本来以为,他会像你一样,喜欢我,但以礼相待,那我跟他同睡一屋也没什么,我们在纳木错还不是这样过了一夜。可刚才一进屋,我发现他、他有那个意思。你知道,不是我多疑,我们女孩子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”。 我明白了。这时候还有什么话好说的,“你甭说了,快叫他过来吧,我开着门等他”。 “你能跟我一起过去跟他说吗?” “这……这样可能会让他觉得很没面子。相信他是个爷们,不会死乞白赖的,还是你自己去说比较好,实在不行我再过去。” “那好吧。谢谢你啊余哥!” “你又客气了。” “不好意思了余哥,你对我这么好,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对了,我明天上午十点的飞机,很早就得走了,不打扰你们休息,就此别过。有机会一定要来成都,我带你好好逛逛,请你吃串串。” “好的,一定去,谢谢。”我言不由衷。林汐嫣然一笑,感激地看了我一眼,放心地走了。 草草撒了泡尿,回到,把门打开,把另一张空床上的行李拿下,等着那姓慕容的过来。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我躺在床上,困意渐袭,他却一直没过来,早知道我就跟林汐过去了。刚才我真的担心,我俩一起过去他会很没面子,男人嘛。要不,我还是亲自过去一下?算了,我这样过去算什么,也许他愿意规规矩矩地陪她呆着,不用再过来了;也许他精诚所至,金石已开…… 就这么胡思乱想,不知道什么时候睡过去的,也不知道睡了多久,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。迷迷糊糊中,我想说门开着,进来吧,话一出口,我耳朵听到的,却是一声口哨。这时,便感觉有一个人影飘了进来,悄无声息。我艰难地睁开眼睛,发现眼前站着的,不是那姓慕容的,而是林汐。她站在我床边,双手张开,有点伤感地说:“余哥,我要走了,可以抱你一下吗?”求之不得啊,我想起身相拥,可不知为什么,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,怎么挣扎都起不来。林汐走近一步,俯下身,双手抱住了我。我又想伸出手,可手也动不了,只好任她抱着。突然,我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,本应是温香软玉的她,怎么手臂是冰凉的?我张开口,却说不出话来,而她的脸瞬间变了形,精致的五官堆在一起,紧接着又挤压、扭曲,眨眼间,一个美女的脸,变得跟藏戏中的恶魔面具一样恐怖,而且那张脸还狰狞地笑了起来。我毛骨悚然,身体却依然一点都动不了。那恶魔般的脸盯着我看了一会,猛地伏在我脖子上,咬了一口,我惨叫一声—— 眼睛蓦地睁开,一下子醒了过来,房里一片光明,原来只是噩梦。下意识摸摸脖子,又看看时间,十点过了,这时候,林汐应该在天上了吧。 另一张床还是空着,枕头被子没有被动过的痕迹。果然,姓慕容的昨晚没过来,那他们……靠,关我鸟事。 04 洗脸刷牙后,我给贺中老师打了电话,他说最快明天回到拉萨,但墨脱那边的路太难走了,不可抗力的因素太多。既然这样,那就继续等吧。出了八廊学,随便吃了早点,信步走到药王山,爬了上去,从另一个角度拍了布达拉宫。下了山,又到八廓街转了转,街拍了一组,又折进一个书吧,舒舒服服看了一个下午的书。 傍晚快七点,感觉肚子有点饿,随便走进一家藏餐馆,要了一壶酥油茶,一碟牦牛肉,一碗饭,慢慢吃起来。 正吃着,电视里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:“西藏电视台记者报道:昨天晚上9点,卡如拉山口发生的雪崩事件已造成了五人死亡及多人失踪,公路交通堵塞近七个小时。五位不幸遇难者的身份已查明,除司机外,还有四位乘客,而失踪的乘客人数及身份至今仍无法确定。至记者截稿时止,由部队和自治区组成的联合搜救工作仍在紧张在序地进行着,但专家估计,失踪者生还可能性很小。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忠告游客……” 卡如拉! 想起来了,姓慕容的昨晚给林汐的短信说,他在卡如拉山口遇到雪崩,车堵了一个多小时! 这怎么可能。 再细一想,冷汗都下来了:9点雪崩,路堵了7个小时,应该是凌晨4点左右才通的车,他怎么可能在1点19分回到拉萨?难道我真见鬼了?口哨真的招魂了? 新闻结束了很久,我还愣愣地盯着电视屏幕,饭也吃不下。如果他真的是鬼,那……那林汐昨晚……我拿出手机,翻到她留给我的电话,拨了过去,关机。只好给她发了条信息:“打你手机关机了,问好,见信请回。” 强迫自己不再想下去。算了,也就一个萍水相逢的女孩,生命中的过客而已。是福是祸,也是她的命。 回到八廊学,门口停着一辆警车。听说前几天这里曾有游客被偷了两万块现金,不知道是不是破案了,还是警察来继续调查。刚走进去,服务台边站着两个警察,正跟服务员询问着什么,服务员看到我,眼神突然像见到鬼,朝警察努努嘴,俩警察转过身来,迅速一前一后夹住我。我还没反应过来,站前面那个严肃地盯着我问:“你是余少镭?” 我点点头。 “跟我们走一趟。” “什么事?”我愣住了。进藏十多天,没干过什么违法的事啊。 “去了就知道了。配合点。” 上了警车,没开多远,我被带进了北京东路上的城关公安分局,一进去,就被收了手机、钱包,又被抽掉了裤腰带,一警察将我浑身摸遍,发现再无其他东西,就把我关进了预审室里。 惶惑、恐惧,我感觉心跳得厉害,手脚都在发抖,脑子里迅速把进藏以来有可能涉及违法的事过了一遍:在西藏博物馆里说了政治不正确的话?在大昭寺里偷拍写着“禁止摄影”的佛像?还是在“念”吧听歌时跟一个外国小伙子聊了几句对时局的看法? 正胡乱猜想着,门开了,一个警察走进来,啪一声把一个文件夹甩在我跟前,然后坐在我对面,打开文件夹: “姓名?”“民族?”“职业?”“籍贯?” 几句例行公事过后,警察用秃鹫一样的眼睛盯了我一眼,问:“知道为什么把你带来这里吗?” 我摇摇头:“我真不知道,能否直接告诉我,我犯了什么法?” 警察嘴角浮起一丝冷笑,说:“每个人来到这里,第一句都是这么说。我们连夜带你来,是你涉嫌跟八廊学旅馆的一个命案有关。我们查过,你也算文化人吧,配合点,我们也不希望搞得太难看。” 命案?!头嗡的一响,谁死了? 那警察盯着我,目光冷若冰锋:“今天中午,一位叫林汐的女游客被发现死在她所住的八廊学客栈房间里。法医认定,她是被人用被子蒙住头脸导致窒息而死,死亡时间在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,而且,死后有被性侵的痕迹。据我们调查,受害人死前跟你在一起,所以目前你有最大的嫌疑,请你交代一下,你这两天干过的一切。” 林汐死了?!我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“不不,警察同志,我知道,我现在怎么说我没杀她你们也不信,可我要告诉你们,昨晚上一直到凌晨两点多,跟她在一起的,还有另外一个人……” 我把此事的前前后后,包括当晚的一切都向警察坦白。当然,我漏过了钦顿老人忠告我别吹口哨的事,觉得那有点荒唐,反正,“念”吧的服务员丹姆会为我作证的。 警察瞪着我说:“我们不会随便冤枉一个好人,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你所说的一切,我们会去调查,但目前你仍然是嫌疑最大的人,所以,我们依法对你进行留置。” 我突然想起那警察刚才说的一句话,赶紧说:“对了警察同志,你说她死后还被那啥了,这样更好……哦不对,我说错了对不起,不是更好,我的意思是说,那她尸体上肯定残留着凶手的什么,你们验一下我的DNA吧,我就可以洗脱嫌疑了。” 他瞪了我一眼说:“你小说看多了吧。少废话,这个还得你来教我们吗?”说着,他打开门,朝外面喊了一句什么,又一个警察进来,给我提了指纹,采了血样,然后就把带进了一间窄小的拘留室里。 拘留室的夜,地狱般黑暗。我没想到这次西藏之行会有这样的倒霉经历。我尽最大努力去相信,警察的调查能证明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,可万一那姓慕容的真的已经在雪崩中遇难,那么,谁会相信,是我的口哨引来了他的魂,而他又把林汐杀了?如果他是人,那么他杀了林汐之后,为什么不把我也杀了灭口? 一夜无眠。 第二天下午,留置室的门开了,昨天带我来的两个警察出现在门口。 “你可以走了余先生。” 这么快? “另一个嫌疑人,就是你说的慕容某某,今天一早前来投案自首了,我们也已经带他去指认了现场,所以你可以走了。” 真的是他!可他既然杀了人,怎么还会来自首呢? 我洗脱了嫌疑,心里却轻松不起来。太多的疑问,如果不弄清楚,余生都会活在这事的阴影里。 “警察同志,我想见见那嫌犯,可以吗?” “开什么玩笑。” “我无缘无故被你们关了一夜,还为你们破案提供了线索。我只想问他几个问题,弄清楚心中的疑问。这个小小的要求,你们就不能答应吗?” “啥无缘无故的,你要是不对人家姑娘起色心,会被卷进这案子吗?省省吧,西藏不是你们艳遇的天堂。这次算你走运,不过,在DNA比对结果出来之前,你还不能离开拉萨,就先住在你担保人家里吧。” “我担保人?谁是我担保人?” “出去就知道了,他在外面等你。”警察的语气明显已不耐烦了。我不敢再叽歪,拿了被扣留的手机等物品,走出了分局。 高原的阳光晃眼,我手扶额正张望,突然背后一双大手差点把我拍了个踉跄,转过身,便见一个高大的汉子,脸上藏不住坏笑,说:“你小子,来西藏泡妞的多了,吃不到羊肉惹一身骚还差点自己弄死的就你一个哈哈哈!”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,正是我要拜访的前辈作家贺中老师,虽然人没见过,但照片我有,果然,真人长得跟历史教科书里的成吉思汗特别像(他真有蒙古血统),没想到,竟然是他来担保我,更没想到,我跟这位我景仰的前辈老师,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第一次见面。 贺中老师真的很像成吉思汗“贺老师,真不好意思,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给您惹了这么大麻烦。” 他一搂我肩膀,嗐,老个屁师啊,我看你比我就小几岁吧,叫我老贺,或者跟别人一样叫我贺老憨都行,你是郝群的兄弟,郝群是我好兄弟,你也就是我好兄弟(郝群也是著名作家,以笔名行世),麻个七八烦,你要真杀了人,我也保不了你,走,到我的酒窝喝酒去,给你压压惊。 上了贺中的吉普,路上,他才告诉了我,怎么会成为我的担保人: 我是那啥,中午回到拉萨就给你小子电话了,没想到是一警察接的电话,很警惕,问我是你啥人,我就知道你小子出事了,开始以为肯定是政治案件,哪想到是桃色凶手案哈哈!你要知道,我在拉萨这么多年,几乎所有警察都是我哥们儿,那警察一听说是我,语气就客气多了,说你卷进了一宗奸杀案,昨晚被抓,不过今天上午,真凶投案自首了,人应该真不是你杀的,但案情未结,你也算证人一个,不能离开拉萨,如果有担保人,可以暂时离开拘留所,我就来了。 原来这样。但我心里还是有诸多疑问,就说贺老……哦老贺、贺中兄,您刚刚说我差点把自己弄死,又是咋回事。 “啊?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啊?那小子,应该也是怂人一个,我给你办手续的时候,听我一哥们儿、刑警副队说,他杀人后越想越怕,精神吓出毛病来了,居然说你有邪术。” “说我有邪术?” “对,他说他跟那女孩从纳木错回来后,其实并没有去亚东,因为他之前还跟另一个女孩有约,所以想先搞掂那一个,再搞掂这个。前天晚上,他等到很晚才出现,是想着那时候已订不到房了,那女孩肯定会留宿他,毕竟他们之前在纳木错就那样过了一晚,这次应该能得手。没想到,你会陪着那女孩等他,而且那女孩会叫他到你那儿住。 “他说他杀那女孩并不是故意的,开始直接约炮,那女孩不同意,他就霸王硬上弓,因为他之前已这样得手过几个女文青,过后都没事,没想到,这一次那成都女孩反应太强烈,甚至喊起来,他想捂住她,手一重就弄死了她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进入你房间想把你也杀了灭口,当时你睡得正熟,他两次近你身,都被你身上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开,吓得当晚就逃跑了。今天一早,他本想逃离拉萨,没想到在去火车站路上遇到俩喇嘛,一前一后堵住他,硬要把一根红绳子往他脖子上套,把他给吓的,越想越邪,就到局子里自首了。这鬼话应该也是他瞎编的吧,我可不信,看你这小子,俗人一个,哪来的什么邪术,还无形的力量呢,该不是你会发射外气吧,哈哈哈哈哈。” 第一次见一个这么魁梧的大老爷们笑得花枝乱颤,可我却笑不起来,虽然现在知道了,姓慕容的不是鬼,但想杀我却被我“无形的力量”推开又是什么鬼?编这个不可能让他减少刑罚啊。我年轻时确曾跟着潮流学过气功,可后来知道所谓的发外气都是忽悠人的,就不再学了,难不成,像武侠小说一样,我其实已打通了任督二脉只是自己不知道,关键时候,“外气”救了我一命?慢着……这该不会是……那啥吧? 一个激灵,把手伸进牛仔裤兜里,果然摸到了一张字条——警察搜我身的时候,应该摸不出来,漏过了它。 掏出来,捋平,纸面虽然更皱了,但那上面的烫金符,似乎在闪着光。 又是一阵鸡皮疙瘩。 难道真是它? “老贺,咱先别喝酒,有个很重要的事,麻烦您先载我回念吧,我要找个人。” 05 黄昏的念吧,没有客人,服务员丹姆正在玩手机,见我进来,愣了一下,又像见到啥不该见的东西,再看到我身后的贺中,笑颜顿开,“老憨叔,您有一段时间没来了。” 贺中指着我说,我这兄弟,想问你个事。 贺中老师是念吧VIP,服务员丹姆见到他都很开心我不多说废话,说你还记得,3号那天晚上,我跟一个女孩在这儿喝酒,后来一个本地老人进来,跟我们一起喝,还讲了个故事,他跟你很熟的样子……丹姆点点头,对啊,钦顿大爷,我当然认识,很热心的大爷,游客有事他都会尽力帮忙,怎么了?我说你知道他家住哪吗,她说知道的,大昭寺后面,仓姑寺隔壁,具体门牌号我记不住,您去那儿问一下,很多人都认识他的。 贺中老师带着我,从大昭寺后面的八廓街走进去,再走了约两公里曲里拐弯的小巷,在仓姑寺门口,问了第一个本地人,他给我们指了指钦顿老人的家,就在不到20米的地方。 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藏族汉子接待了我,一看长相,不用问就知道是钦顿老人的儿子。 我说明来意。汉子眼睛一红,用生硬的汉语说:“我爹他、他下午刚天葬了。” 啊?! “他老人家什么时候过、过……往生的?” “9月3号,他去亚东贩羊皮回来,路上遇到雪崩,车翻了,不幸遇难。” 9月3日!我跟贺中老师互相看了一眼,他的眼睛也瞪得牛铃般大。我哆嗦着从兜里把老人给我的那张符掏出来,给他儿子看,“可这是9月3日晚上,老人家送给我的啊。” 他接过一看,点点头,“嗯,这是仓姑寺的师父们画的,能辟邪,我爹求了一些,经常拿它们送人,特别是外地来的游客。” 后来我去了仓姑寺,看到师太们在制作各种经纸、符咒“这符到底是什么意思?” 他说:“这不是符,是金刚上师咒:唵阿吽班杂咕噜叭嘛悉地吽。用汉语说,这个咒的意思是:‘我启请你,金刚上师,莲花生大士,以你的加持力赐给我们一般和无上的金刚法力。’这个咒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。我爹把这个咒给您,是希望您能避开一切邪恶的侵犯。” “可你说他是9月3日去世的啊!” “先生,您还不明白吗,我爹路上不幸遇难,灵魂赶着回家,刚回到拉萨,对了……” 他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,瞪大眼睛问我:“那天晚上,您是不是吹口哨了?” -END- 余少镭个人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yangtijiaa.com/ytjzp/724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已成行5月31徒步新疆天山最美雪山
- 下一篇文章: 推荐好听的宝宝取名参考,德才兼备的名字给